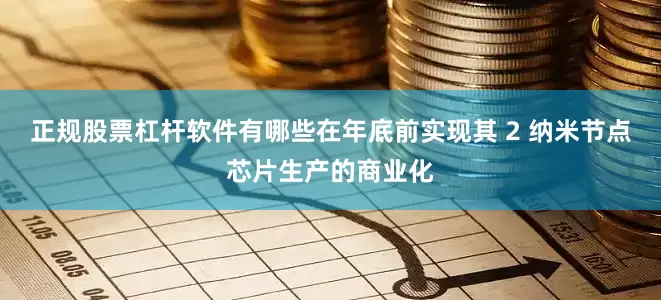1945年12月15日,滕海清率领新四军第九旅将陶庄团团包围,一场激战即将拉开序幕。正当此时,军长陈毅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了指挥所。面对这位资深首长,滕海清旅长却毫不拘礼:“军长,今日之战,您就交给我来指挥吧。”

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的初创军长,滕海清以其作战之勇猛与策略之灵活,在人生旅途中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。其中,倪志亮将军堪称他人生道路上的首位伯乐。
滕海清,生于1909年,籍贯安徽省金寨县。投身红军后,他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。凭借出色的作战表现,滕海清仅用两年时间便晋升为三十二团五连连长。
在一场激战中,滕海清夺得两匹枣红战马。滕海清心有所思,既然自己已晋升为连长,若仍不擅骑术,实有不妥。于是,他决定暂将这两匹马收于麾下,待熟练骑术之后再行上交。
正当此时,滕海清不期而遇了自己的上级——倪志亮。倪志亮注意到滕海清独自驾驭两匹骏马,便好奇地问:“你是哪个部队的?”
滕海清回应道:“我属于三十二团,担任五连的连长职务。”倪志亮接着询问:“你为何驾驭了两匹马?”
滕海清灵机一动,回应道:“哦!我来是替师长和政委牵马的。”
倪志亮闻言,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:“这小伙子真机灵!”随即,他吩咐自己的通信员将那两匹马牵走。
倪志亮离去后,滕海清心中充满了不安,他害怕师长可能察觉到了自己的小心思,是否会受到纪律上的惩处。十天过去,他焦虑的情绪得到了证实,营长通知他:“滕海清,立刻收拾行囊,前往师部报到。”
“并非我个人的意愿,而是团部下达的调动命令。”
滕海清手持介绍信再次拜访团长程启光,询问道:“此次调令是何意图?”团长回应:“详情不明,仅因师部之命。”

滕海清紧握着由部队开具的介绍信,心怀激动地抵达师部驻地,步入了师长和政委的办公室。倪志亮浏览完滕海清的介绍信后,开口询问:“此次调你至师部通信队担任排长,不知你是否有所异议?”
滕海清回应道:“并无任何不快,无论从事何事都无妨。”即便“降级”了,他仍旧心怀感激,庆幸自己并未受到纪律上的惩处。
然而,尽管通信排的工作已经持续数月,滕海清却意外地发现,自己并未遭遇“降级”,反而迎来了晋升。原因在于,师部的通信排性质独特,仅由两个排组成,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排。其中一排,空缺的士兵位置由未能出色完成战斗任务的营连干部填补;而二排,则是由各团精心挑选出的优秀班长组成,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后,便被分配至各连队担任排长。
简而言之,通信排的角色恰似教导队,它是培育未来基层军官的摇篮。滕海清所负责的队伍,规模甚至达到了一个加强连,数量上并不逊色于往昔。唯有在精英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,才有幸担任通信排的排长之职!
倪志亮并非首次展现出独具慧眼的识人本领。尽管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,他仅获中将头衔,然而他麾下曾经汇聚了一批杰出人才。这些人才中,涌现出了众多开国元勋,诸如王宏坤、王新亭、李天焕、胡奇才、陈再道、孙玉清等。其中,王宏坤、王新亭和陈再道均荣膺上将军衔。而滕海清的表现,更是充分验证了倪志亮眼光的精准无误。
1932年10月12日,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,于平汉线上遭遇卫立煌、胡宗南指挥的6个师的围追。面对敌军人数上的绝对优势,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激战。当战局陷入胶着之际,滕海清率领通信排的勇士们奋勇当先,与敌人展开了惨烈的近身肉搏。
在奋勇前行的征途中,敌人掷出一颗手榴弹。在这瞬息万变的电光火石之际,滕海清未能及时躲避,不幸遭受了严重的爆炸伤害。火药的烈焰烧伤了双眼,几乎使他的视力几近丧失;弹片不仅打落了他的门牙,还穿透了他的右臂。

在长征途中,敌军遍布,依据军规,重伤无法行动的战士需被安置于当地村民家中。滕海清紧握着首长所赠的十枚银元,心中失落不已。“革命尚未胜利,我怎能舍弃红军?”他悲痛欲绝地哭喊道:
“我立志投身革命,革命的理想仍在我心中熊熊燃烧,我绝不能放弃革命的武装,就此黯然退场!”
滕海清因眼部受伤,视力所剩无几。他手拄拐杖,孤独地行走,缓缓地尾随大部队。夜幕降临,滕海清终于追上了后卫部队。当他听说野战医院设在前方的山丘之上,心中顿时充满惊喜,激动地喊道:“我要见院长!”
循着那熟悉的声响,倪志亮亦步亦趋来到了野战医院。面对滕海清,倪志亮眼中闪过一丝恍然大悟,随即对院长严肃地说:“通信队的排长负责管理营连干部,其职位相当于副团级,因此,您需按照营级以上伤员的待遇来对待他。”
在倪志亮的悉心扶助下,滕海清得以留在军中。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,尽管他不幸失去了左眼,但最终康复如初。康复出院后,滕海清重返师部通信队,重新回到了他的军事岗位。
抵达四川后,倪志亮将滕海清委派至四连场周边地区负责“扩红”工作。滕海清仅以一个月的辛勤努力,便将游击队的人数从最初的两人迅速增至三百余人,充分彰显了他的卓越组织能力。随后,该游击队升级为正规部队,其原游击一连被改编为红三十一团的特务连,滕海清则担任连长兼指导员。
1933年十月,红四方面军面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。四川军阀刘湘集结了二十万大军,对川陕苏区展开了六路围攻。在这场激战中,滕海清率领特务连冲锋陷阵,屡建奇功。然而,在这场战斗中,滕海清不幸再次身中弹丸,重伤垂危,子弹自喉部射入,险些夺去他的生命。幸而他体魄强健,终于顽强地挺了过来。

自此,滕海清与他的首位恩人倪志亮依依惜别。1965年,滕海清重返北京301医院,拜访他的恩师——倪志亮。尽管岁月流逝,倪志亮仍能一眼认出滕海清。然而,面对往日的栽培之恩,倪志亮却未曾提及,反而向他致歉道:“当年我身上尚存一些军阀习性,时有辱骂与体罚之事发生。”
滕海清却带着笑意说道:“老首长,记得我曾是通信排长那会儿,您还曾严厉地批评过我两次。那些往事,我早已淡忘,如今回想起来,却都成了珍贵的记忆。您是我敬重的首长,我从未有愧于您的栽培。”
历经长征的磨砺,滕海清步入了神圣的抗日战争战场。彼时,他已荣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教导大队的大队长。1938年3月,滕海清被调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执行任务。竹沟镇被誉为“小延安”,得益于当地一位杰出的革命家——彭雪枫将军。彭雪枫将军因此成为了滕海清的又一恩人。
“昔日你在红军中身担团政委重任,我深信将部队交付于你,便足以安心。你必须悉心培育这支队伍,因为它是我军东征豫皖苏,投身革命事业的关键所在。”
须知,第二大队乃彭雪枫自竹沟精心挑选而组建的精锐之师,此中可见他对滕海清的深厚信任与重视。滕海清日后曾多次向他人提及:“
“彭司令员对我所展现的信任,不仅是一种缘分的体现,更是革命战友间深厚的情谊。我心中暗自立誓,定要使第二大队声名远扬!”

在随后的激战中,滕海清不负彭雪枫的重托,屡战屡胜,在鄂豫皖地区声名鹊起。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,彭雪枫与黄克诚的部队合并,组建为八路军第四纵队,下辖四个旅。彭雪枫担任司令员,黄克诚则出任政治委员。滕海清则被任命为第五旅旅长。1941年1月,皖南事变爆发后,第五旅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,滕海清与孔石泉分别担任旅长和政治委员。
因此,彭雪枫亲手组建的部队,悉数移交给了滕海清指挥。在彭雪枫的悉心培养与关照下,滕海清如同蛟龙得水,战场上的指挥才能愈发纯熟,令日伪势力闻风丧胆。
1940年11月,日本驻徐州的第十三军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,连同蚌埠、宿县等地的日伪军共计五千余人,乘坐70余辆卡车,配备20余辆坦克,对涡阳、怀远地区发起了规模庞大的攻势。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,当地国民党军队见状纷纷撤离原有防区,退守至太和、阜阳一带。
彭雪枫洞察先机,断言日军必将对板桥集发起进攻。因此,他叮嘱滕海清,务必率领第五旅坚守板桥集,抵御日军的进攻,并给予友军有力支援。
板桥集位于蒙城县二十五公里之外,是一个交通便利、商业繁荣的集散地,其战略地位尤为显要。在抗日战争中,我军作战以游击战为主,鲜少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战。然而,此次滕海清审时度势,巧妙地利用了板桥集的地形优势,决定与日军展开一场真正的交锋。
在滕海清的指挥之下,五旅各团全面开展工事大修,构筑了坚固的碉堡与蜿蜒的交通壕,将各个掩体紧密相连,令板桥变身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。
11月16日,五百余日军及一千余伪军沿宿蒙公路进犯板桥集,与此同时,徐州与蚌埠的日伪军亦汇聚于南坪周边,对板桥集构成夹击之态势。
17日,日伪军依仗其兵力和武器上的优势,对板桥集发起了猛烈的攻势。敌军不仅动用了坦克和大炮,还出动了数架飞机,对我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。炮火准备过后,日军随即指挥伪军冲锋在前,意图使我军弹药消耗殆尽。面对此情此景,我军毫不示弱,将这些民族的败类击杀得尸横遍野。
日军目睹伪军战斗力已近尾声,便在炮火支援下,狂吼着向我军阵地发起了猛攻。我军毫不退缩,以刺刀和手榴弹还击敌人。直至黄昏时分,滕海清察觉到敌众我寡,面临被敌人合围的险境。为确保实力,滕海清率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,沿着抗日沟撤退至板桥集西北的大赵庄,与前来支援的友军汇合。而日军趁机占领了板桥集。

得益于友军的援助,滕海清迅速在当日对板桥集的敌军发起了反击。但那晚,明月高悬,而日军亦擅夜间作战,我军虽连续发动数轮攻势,却未能取得胜利。于是,滕海清率领部队向南坪地区转移。
行进过程中,滕海清部与驻扎于徐州的日军遭遇,一场激战一触即发。滕海清迅速作出决策,命令部队抢占制高点,给予敌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。
尽管敌军拥有飞机与坦克的支援,新四军却展现出非凡的勇气,激战从夜幕低垂持续至曙光初现,日军遭受重创,被迫丢弃了受损的坦克与卡车,向西溃逃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在敌机来袭进行轰炸之际,机枪手陈金富巧妙地将苏制机枪置于弹药手李鸿立的肩上,两人藏身于一棵大树之下,对敌机进行精准射击。紧接着,其他几位机枪手如李卓明、常祥等亦纷纷将机枪对准天空,对敌机发起猛烈的扫射。不久,一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在黑烟滚滚中坠地,机上的三名日军士兵随即命丧黄泉。
机枪成功击落敌机,这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。除击落敌机之外,我军还一举歼灭了1200余名日伪军。战后,十八集团军总部及彭雪枫、张震等首长均对滕海清及其部队给予了高度赞誉和鼓励。国民党第一战区亦不得不承认,我军所取得的战绩令人惊叹。
至1944年,抗日战争的形势已显著改善,新四军第四师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攻行动,成功攻克了众多日军的据点。9月9日,第四师决定对八里庄之敌实施攻势,此次彭雪枫将军亲自挂帅出征。
“不妨让我的第十一旅担当此役!”
彭雪枫深知滕海清连续数月奋战,身心疲惫至极,因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的请求。翌日清晨,滕海清只能默默目送彭雪枫离去,以至于连一声告别的话语都未能及时表达。不幸的是,在9月11日的八里庄战役中,亲临战场的彭雪枫不幸遭受弹雨袭击,英勇牺牲,年仅37岁。

悲讯传来,素以“默默承受,不言牺牲”著称的硬汉滕海清终难掩心中悲痛,站在彭雪枫安卧的办公室,他泪水横飞,失声痛哭。
“师长,您就这样离我们而去……从此,我们再难并肩行军、共战沙场。我们定要为您讨回公道……师长啊,师长……”
众人动容。
滕海清再也无法目睹这位他由衷敬佩的首长、亲切的兄长以及无价的良师益友。
首长虽已英勇献身,但战事仍需继续。陈毅军长,成为了滕海清所识英才中的佼佼者。陈毅率军穿越朱坝的壮举,早已成为流传于世的佳话。然而,若非滕海清的精心护送,陈毅恐难有此辉煌战果。
1944年11月,中央对新四军第四师实施了改组,滕海清同志由此前所属的11旅调任为第9旅的旅长。随着日军的投降,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立的新四军“北进扩展,南守稳固”的战略指导,滕海清与康志强共同率领第九旅踏上了北上的征程。在上旬的十月,部队抵达了位于山东邹县东南地区的集结地。
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,日伪军坚决拒绝向新四军投降,坚持要待国民党军队抵达后才交出武器。即便日军最终投降,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陶庄仍牢牢控制在日伪军手中。

在我军备战进攻之际,旅部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——正是陈毅军长。彼时,陈毅身兼新四军军长与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要职。滕海清一见军长莅临,便好奇地询问:“军长,您怎么亲自来到前线?”
陈毅带着轻松的微笑调侃道:“是不是觉得官位越高,人就越显尊贵?”实则,陈毅此行正是为了亲自督战。
康志强政委强调道:“这并非仅关乎您个人,而是涉及全局的重大议题!”
“我这就给你下面条。”
用过餐后,陈毅言道:“我颇感疲惫,能否寻个地方让我小憩片刻?”然而,滕海清此番却并未留情面,直言道:
“此处并无安寝之地,还请自行返回家中就寝。”
彭雪枫的英勇牺牲,令滕海清深受触动。他不愿再目睹心爱的首长在沙场之上献出生命。见陈毅依然没有启程的迹象,他郑重地开口道:
“司令员,我始终坚定地贯彻您的命令!今日,我愿听从您的指挥!”
陈毅见滕海清意志坚定,便笑着说道:“你们这帮人,强迫与命令的手段已足够高明!”言罢,陈毅在战士们的簇拥下,踏上了离别的征程,远离了前线。
陶庄战役落幕之际,第九旅历经改编,摇身一变成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,由罗炳辉出任纵队司令,而滕海清则继续执掌第九旅的帅印。至1947年1月,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实现合并,第九旅正式更名为第六师。在此期间,滕海清与康志强分别被任命为第六师的师长与政治委员。同年10月,滕海清受命调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的副司令员。

翌年二月,陈毅以其识人善任的慧眼,命滕海清重返旧部,担任第二纵队的司令之职。在华东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,华东第二纵队屡次建立赫赫战功,于宿北、莱芜、孟良崮等关键战役中均贡献了显著的业绩。
在淮海战役的烽火中,滕海清将军率领的二纵部队驰骋千里,转战1500余公里,与敌军激战40余次,成功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○七军军部及其下辖的二六○师、二六一师;第七十军九十六师、三十二师、一三九师;以及第七十二军、第五军、第十二军、第十六兵团、第六兵团的部分兵力,共俘获国民党军士兵3.65万余人。
1949年二月,华东野战军更名为第三野战军,原二纵部队亦改编为21军,滕海清由此担纲该军首任军长之职。在渡江战役胜利之际,滕海清率领21军成功解放了杭州。随之,他被任命为21军军长并兼任杭州警备司令。然而,这一职务仅维持了三天,滕海清便遭到了免职。
“你可谓是古今中外任职最为短暂的城防官员。”
1955年,滕海清荣膺中将军衔,此后历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、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、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。1997年,滕海清在北京逝世,享年88载。
千里马虽多,伯乐却难遇。滕海清能从一名普通战士跃升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,不仅凭借其战场上的智勇双全,更得益于倪志亮、彭雪枫等众多首长的栽培与举荐。正是这些领导者的独具慧眼,识别并提拔了无数英才,使得人民军队人才济济,于革命烽火中展现出独特的光辉。
专业配资论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